《故事》撞沉《太平轮》
| 编辑: 陈豪 | 时间: 2014-12-15 10:49:31 | 来源: 东方早报 |
我们还可以质疑,为什么《泰坦尼克号》可以把人物群像的来龙去脉与船上的故事主线细密交织,要阶级有阶级要爱情有爱情,而《太平轮》就非要拍成上下集。发展了这么多年的影像叙事,顺叙倒叙插叙闪回都放在那里,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你何苦还要上下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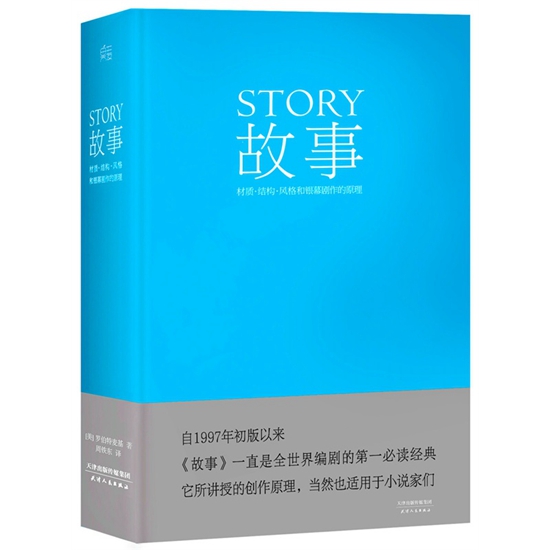
《故事》[美]罗伯特·麦基著周铁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544页,68.00元

《太平轮》在起锚之前,差不多已经被《故事》里的所有创作定律结结实实地撞沉。
《西雅图未眠夜》是不是一部爱情故事片?这个看起来不可能有异议的问题在罗伯特·麦基的《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中却得出了别样的结论。男女主人公的相遇发生在影片末尾而不是开头,所以“这并不是爱情故事,而是渴望故事,因为关于爱的谈论以及爱的欲望充斥了所有场景,将真正的恋爱行为及其不无磨难的后果留到银幕之外的未来发生。也许事实是,二十世纪亲手创造却又埋葬了这个浪漫时代”。
这一段出现在《故事》第三章“结构与背景”中,用来说明如何“向陈词滥调宣战”,如何在精通类型的基础上“再造类型”。可以给麦基补充的一点是,《西雅图》中反复提及并致敬的另一部电影《金玉盟》,正是被《西雅图》的编导诺拉·艾弗朗“精通”并“再造”的类型经典。《故事》写于1997年,如果麦基今年碰巧看到了宁浩的《心花路放》,或许会乐于在他来中国开高价培训班的时候再“现挂”一两句。《心花》从一开始就按男女主角两条线分开叙事,让熟记《西雅图》的文艺青年胸有成竹地认定:黄渤和袁泉一定会在影片的某个时间点邂逅于大理,很可能是在结尾。我们没有猜错,他们确实在结尾才相逢,但宁浩利用蒙太奇时态陷阱玩了一把《西雅图》的逆向结构:他们的邂逅其实发生在几年前,你以为同时进行的两条线其实处在不同的时空中。袁泉站在过去,渐渐向那场“邂逅”靠近;黄渤立于当下,打着公路猎艳的幌子收拾当年“邂逅”造成的心理残局。至于麦基所说的“真正的恋爱行为及其不无磨难的后果”,同样被留到了银幕外,发生在这两段时空之间。随着结尾黄渤在旧爱的婚礼上以相同的程式邂逅新欢,旧故事的幻灭便与新故事的开端完成了重叠,而前者又对后者的未来构成反讽。如是,这一路其实走完了一个封闭的圆环,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麦基在《故事》一书中所赞赏的“故事达到负面之负面”。
在故事的王国中,爱情类型显然是被征用最多、资源近乎枯竭的领地之一,因而说书人在这块领地上的每一次破茧重生都格外艰难。我们重走从《金玉盟》到《西雅图》到《心花》的那条暗道,约略可以窥见编导在拿捏分寸时的如履薄冰,在观众对故事的原始模型(archetype)的心理依赖和喜新厌旧之间寻找愈来愈窄的交集——这差不多也是《故事》一书在各个章节中用不同节奏反复吟唱的主旋律。
与其他论述戏剧文学或者创意写作的书籍相比,《故事》几无学术创见,也不像很多大作家的文学演讲那样充满不可思议的比喻和如同天启神谕般的使命感(想想《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吧)。甚至,在有些段落,它浅近得有点拿不住范儿,激情上头时会来十几个排比句(“对故事的爱……对真理的爱……对知觉的爱……对梦想的爱……”),多少透出一点“成功学”文体的影子——当然,你也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戏仿。麦基从不讳言他本人的编剧经验并不丰富而且水准只能算二流(但他认为,这并不妨碍其成为“最好的编剧教练”);同样地,在这本书里,他在表述观点时也基本上不会含糊其辞。比方说,尽管在划分类别时也算面面俱到,尽管说过不少英格玛·伯格曼的好话,但麦基对电影行业的“高大上”区域总体上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对欧洲片、新浪潮、反情节、作家电影之类的概念也不无揶揄。随手翻翻,就会有这样的冷枪冒出来:“反情节的制造者对欲语还休的描写方式或暗度陈仓式的收敛几乎没有兴趣,相反,为了昭示他的革命雄心,他的影片倾向于过度铺陈和自我意识的大肆渲染。”
也许,正是这种旗帜鲜明的态度,赋予了这本书最显著的特点:在他近乎布道般的鼓吹中,在他熟谙现代商业法则的推销中,企图重建的是人们对故事的信仰——无论这种信仰里含有多少功利的成分。麦基知道,你跟现代人追溯荷马、拉伯雷,缅怀大树底下的说书人,他们会一脸漠然;但是如果你煞有介事地拿出一组图表,卖力地为他们计算盈亏比,指导如何解放故事的生产力,催眠效果就会立竿见影。所以我们常常能在《故事》中看到仿佛能精确量化的句子:
“随着故事设计从大情节开始向下滑行到三角底边的小情节、反情节和非情节时,观众的数目将会不断缩减。”“一个故事,即便在表达混乱的时候,也必须是统一的。” “根据行家的经验,主情节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必须在讲述过程的前四分之一时段内发生。”“一个重复的情感只能产生预期效果的一半,如果再重复一次,其情感负荷就会不幸发生逆转。”“主人公必须具有移情作用,同情作用则可有可无。”“一个故事中两个最强烈的场景往往是最后两幕的高潮,在银幕上,它们常常仅隔十到十五分钟,因此不能重复同样的负荷。如果主人公得到了他的欲望对象,使最后一幕的故事高潮成为正面,那么倒数第二幕高潮则必须是负面。你不能用上扬结局来铺设上扬结局,也不能用低落结局来铺设低落结局。”“改编的第一条原则是:小说越纯,戏剧越纯,电影就越差。”
这些“必须”或“不能”是否能涵盖所有的故事形态,究竟有多少可操作性,其实很难一概而论。同样地,《英国病人》和《三十七度二》(书中译作《巴黎野玫瑰》)的拥趸(我就是)也一定会因为麦基对这两部电影的偏颇之词而略生反感。我们甚至完全可以抛出那个万能的句子——“故事永远存在另一种讲法”,来抗议麦基妄图垄断“故事话语权”的野心。不过,好玩的是,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每当我准备质疑麦基的投机取巧时,总会被某些扰人的观影经历逼回他的文本前,并在心里暗暗承认:如果能做到三成,那么,我国影视行业的优等生未必会增加,但及格率还是有可能显著提升的。换句话说,跟着麦基未必真能学会怎样讲出一个好故事,但起码会比以前更容易辨别一个坏故事。
比方说,差不多已经成为今年国产剧新标杆的《北平无战事》,为什么仍然在很多方面让人骨鲠在喉?大量细节不靠谱、节奏拖沓、场景转换迟滞生硬,这些问题到底能否与其借古讽今、激动人心的“大概念”(big idea),抑或代表国家级水准的表演割裂开来看?当我们随口说上一句“瑕不掩瑜”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些“瑕”的产生,很可能就是因为“瑜”先天不足,有许多失真的,甚至互相矛盾的细节塞进了或许并不成立(至少,其是否成立尚有待论证)的故事框架。如果剧本提供的东西不够扎实,那么演员就只能调动更多的“演技”去凭空发挥,有时漫无边际,有时歪打正着,但都会像显微镜一样放大故事本身的空洞——甚至可以说,演员越好,演技越精湛,这种放大效果就越明显。一个故事,如果光有“道路自信”而没有“细节自信”,那么就只能采用单一的手法反复灌输宏伟的主题。因此,并不是建丰同志除了打电话不会干别的,而是讲故事的人只顾着被自己的理念所感动,却忘了手里缺乏足够的材料来贯彻这种理念,支撑不出更形象更有说服力的细节来推动情节发展。按照麦基的说法,一切陈词滥调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原因,而且也是唯一的原因:作者不了解他故事中的世界。造成“索然无味的讲述”的原因,往往是知识的肤浅。
在这方面,《太平轮》的问题比《北平无战事》要严重好几个数量级。在片中的船起锚之前,差不多已经被《故事》里的所有创作定律结结实实地撞沉。当片中所有人物都在八十年代的节奏中“起范、音乐、定格”时,我们只能报以叹气、哄笑或者睡觉。我们当然可以嘲笑宋慧乔只会光着脚转圈,谴责黄晓明只会歪着嘴微笑,说他们只偶像不实力绣花枕头一包草,但我们更得问一问,编剧究竟给人物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在麦基看来,人物的塑造与故事的结构根本就是一回事,漂亮紧凑的故事线自然会把处于压力之下的人物的本性一步步揭示出来,反之亦然。同样的,对白的好坏与故事的优劣也密不可分,“一个手法精巧而对白粗劣或者描写枯燥的故事是非常罕见的,更多的情形是,故事手法越是精巧,其形象则越生动,对白也越尖锐。故事进展过程的缺乏、动机的虚假、人物的累赘、潜文本的空洞,情节的漏洞以及其他类似的故事问题,才是文笔平淡乏味的根本原因。”所以说,当我们从长泽雅美的信、黄晓明和宋慧乔的日记以及片中绝大部分人物的对话里听不到哪怕一个新鲜的、冒着活气的句子时,我们首先应该怀疑的,不是“编剧的作文是体育老师教的”,而是“他(她)根本没做好编这样一个故事的准备,他(她)不知道笔下的人物应该说什么”。
一觉醒来,走出影院,当我们摘下那副本来就多余的3D眼镜时,我们的耳边可以配上来自《故事》的画外音:“故事讲述已经沦为徒有其表、令人炫目的声光奇观,以免观众注意到故事本身的虚空与伪劣……银幕充斥着华彩的摄影和用金钱堆砌的制作场景,然后用一个单调低沉的画外音将形象串联在一起,将电影这门艺术蜕变为过去曾经风靡一时的经典连环画。”如果用这段话来形容《太平轮》,惟一需要修改的地方,是把“声光奇观”改成“婚纱摄影式的廉价审美”。进而,我们还可以质疑,为什么《泰坦尼克号》可以把人物群像的来龙去脉与船上的故事主线细密交织,要阶级有阶级要爱情有爱情,而《太平轮》就非要拍成上下集。发展了这么多年的影像叙事,顺叙倒叙插叙闪回都放在那里,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你何苦还要上下集?除了想多赚点票房,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于是麦基的告诫再度响起:“我们习惯性地推迟主情节,在开篇序列中一味地充塞一些解说性的东西。我们一贯地低估观众的知识和生活经历,用烦琐的细节来展示我们的人物及其世界,而对于这些东西,观众往往仅凭常识便能知晓。”
“观众往往仅凭常识便能知晓。”这样的说法是典型的麦基风格。事实上,“说书人”如何评估他们与观众的关系,也是《故事》中一个重要而有趣的命题。麦基始终把两者置于一场动态平衡的拉锯战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然,鉴于麦基是重建故事信仰的布道者,在他的暗示中,这场拉锯战的最终胜利者当然必须是说书人。为此,他不惜用了两个略显轻浮的比喻:其一,中世纪的农民偷猎鹿和松鸡后,带着战利品穿过森林逃跑时,他们会用一条鱼,一条熏鲱鱼,在逃路上横拖一下,以迷惑庄园主的猎犬。可想而知,这里的“猎犬”指的是观众,而好故事的作者,一定要准备好那条香喷喷的熏鲱鱼。其二,房中术大师们都知道把握做爱的进度,在“只差一点儿”的时候讲个笑话,换个位置,吃个三明治,“以周期性升降的紧张度”达到欲仙欲死的境界。
“宽厚仁慈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在和我们做爱啊,”麦基写到这里,已经忘乎所以,“他知道我们有能力达到那样的高潮……如果他能掌握好适当进度的话。”
相关新闻
新闻推荐
- 中国代表:日本殖民统治是台湾历史最黑暗一页2025-12-19
- 数据印证海南对全球资本“磁吸力” 解读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含金量”2025-12-19
- 国民党和民众党民意代表宣布将提案弹劾赖清德2025-12-19
- 骐骥驰骋!2026年总台马年春晚吉祥物发布2025-12-18
- 高市涉台答辩遭日本在野党追问 国会多次中断2025-12-18
- 多国人士: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释放投资便利 共享中国市场新机遇2025-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