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令过去不可能的研究成为可能
| 编辑: 张旭 | 时间: 2020-03-15 17:58:34 | 来源: 文汇报 |
美国史学家访谈系列的受访人大多是成名学者,但较少出现年轻人的声音,人们也很少了解美国普通高校的博士毕业生在学界的成长经历。尼克·萨姆巴拉克(Nicholas Michael Sambaluk)是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我们做访谈时,他刚刚博士毕业不久,在普渡大学军事科学和技术实践部工作,兼任西点军校网络战研究所的研究员(the Army Cyber Institute at West Point),第一次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独立书房,并刚刚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尼克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史、军事史和国际关系史。我们在一家喧闹的咖啡馆里完成了这篇访谈,时隔四年,我至今仍记得他谈起军事史研究时那种兴奋的神情,使我感到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以此为业,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之后每一次去华盛顿的航空航天博物馆,我都会想起尼克和他对军事史研究的激情。尼克对于新军事史的研究和教学,或可以给国内有同样研究兴趣的朋友以启发。

尼克·萨姆巴拉克在飞行器前留影
研究最开始要注重结构,它是激情的产物
很高兴您参与这次访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学术背景,您怎么对历史感兴趣,进而立志成为一位历史学家?
尼克·萨姆巴拉克:我大概生来就喜欢历史。四岁那年,我第一次去华盛顿的航空航天博物馆,就表现出对历史的浓厚兴趣。那是一座很棒的博物馆,展出早期飞行器,我经常跟朋友谈论这些炫酷的展品。我从小就阅读了很多航行器的著作,乐在其中,也喜欢读历史书,一有空我就徜徉在书海之中。在六年级时,我遇到一位好老师,她曾鼓励我,让我与一群思考历史、对历史充满激情的人一起讨论。我喜欢那段经历,现在仍然跟她保持联系。我的书出版后她很为我感到高兴。这些特殊而又意义深远的机遇成为我人生中最好的回忆和经历。2014年春,我成为一名老师,带着学生去华盛顿航天博物馆。我们边浏览,边讨论它如何呈现历史记忆,如何从专业角度解释历史。
您在堪萨斯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在博士班的经历?
尼克·萨姆巴拉克:我在堪萨斯大学主攻美国史和军事史,辅修国际关系史。我接受了美国和欧洲不同的研究生培养方式,它们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之处。
我最一开始在得克萨斯大学学习核心课程,并在系里做助教,主讲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如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等;后来我在曼彻斯特学习了几年。大部分人要修三年,但我想尽快毕业,就额外上了六门课程,只用了两年就毕业了。在得克萨斯大学倒数第二学期,我的导师(阿德里安·刘易斯[Adrian Lewis])决定去堪萨斯大学工作。我要决定是否与导师一起去堪萨斯,同时,还得负责给学生上课,重新安排论文小组,为了论文写出新意还得学一门新语言。我发现自己真正想研究的是军事史,希望将技术史和军事史结合,研究其对世界的影响。经过深思熟虑,最终我决定跟随导师去堪萨斯。
我先在堪萨斯大学上了两年课,紧接着在2010年夏秋开始做档案研究。到2011年,我用了十一个半月完成了论文。随后,在攻读博士的最后一年,我全身心投入到授课当中去,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给佛罗伦萨、巴黎、斯洛文尼亚等地的学生讲课,这些都是我论文中涉及的城市和国家。我讲授从1945年至今的世界当代史。首先以时间为序,讲述欧洲历史,还有一部分超出了欧洲范围;接下来是冷战,从巴黎视角看待冷战是全新的体验;此外,我还跟学生分享全球技术的非殖民化等内容。我曾与学生一起去巴黎的各种博物馆。在艺术博物馆,我给他们讲解法国的军事史;我们一起参观位于巴黎的欧洲最大的大屠杀纪念馆;最后我们一起浏览政治博物馆,实地考察奥马哈海滩的诺曼底登陆。在难得的海外授课中,我依照自己的兴趣设计新课程,我把其中一些内容和方法运用到未来的课程讲授之中,如2015年我给学生讲美国内战时期的技术和发明,其方法和主题非常吸引人。
接下来我们聊聊您的博士论文。从堪萨斯毕业三四年后,您就出版了论文。能否请你谈谈在论文撰写和出版过程中的经历?
尼克·萨姆巴拉克:我在2012年5月毕业,三年半后,我的书出版(The Other Space Race:Eisenhower and the Quest for Aerospace Security[Transforming War],Naval Institute Press,2015)。
讲课和利用档案做研究是不同的,前者并非创造一个新领域,利用档案撰写论文则需要极大的热情和决心。我曾去不同档案馆研究档案,如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呆了三四天,花五天时间在阿拉巴马档案馆,一周时间用在国家航空和宇宙飞行局(NASA),堪萨斯档案馆用了两周。在档案馆中我拍了很多照片,回去后把它们整理出来,作为我论文的素材。
在读书期间我曾获得过两条宝贵建议。第一条是,如果你对某个历史问题感兴趣,经过调查你发现其他人尚未关注到,那么就要重视它,因为这值得你去努力,乃至成为你学位论文的选题,甚至有可能成为你的第一本书。我得到这条经验已经很晚了,差不多是定下论文主题前几周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所有研究生一入学就应该知道这一点,这会让他们激情满满地做研究。
第二条经验是,要善于提问。我最初上研究生课程的时候相当挣扎,因为研究生从来不提问题,甚至有的人觉得不应该发问。这糟糕透了,对你的研究来说,积极思考是最好的方法了。例如,我会跟周围人讨论美国空间项目建立的故事,在这期间不同的人的态度及其冲突,未来的计划和政策等。在我着手写论文之前已经研究了很多与论题相关的内容,在调查和与他人讨论中发现了很多为前人所忽略的问题,通过提问发现新问题,最终形成了论文的核心主题。
我认为研究最开始要注重结构,它是激情的产物。你要投入足够多的热情,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一个基本结构。出于对论文的组织和表达的考虑,你得随时做调整,但是对其总体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结果,则不那么确定。我最初想探索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空间政策和项目,根据我们的印象,那个时期人类都在探索太空的奥秘,这是我感兴趣的领域,也得到了导师的支持。做自己喜欢的领域和问题才会有更多的激情帮助你更好做研究。
具体而言,我在2010年4月2日修完了课程,打算2012年春季申请助教给学生讲课,因此我必须在这期间完成论文。于是,我在2010年尽可能搜集核心档案,然后主要在2011年撰写论文。我注意到很多人都花费很长时间撰写论文,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时间表,从2011年1月1日开始,计划每个阶段写多长时间,离完成计划还有多少工作量,一目了然。我的计划是一周写五天,每周一、三、五和周末,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写作,一直写到中午吃饭,用选题不断刷新自己的头脑,使之保持活跃,因此对我来说论文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但为了确保自己有时间思考,我不能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于是每周有两天放空时间,等到再回到论文写作的时候,在很短时间内可能有更大收获。在周二和周四我会远离论文,而花时间读很多书。这是学位论文的撰写方式,可能不适用于撰写书籍。
后来论文出版前我与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 Press)联系,那是一家很好的非虚构出版社,与我的论文主题非常契合。他们喜欢我的选题,给我设计了很棒的封面。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缩减文字,保留了史料,最后在2015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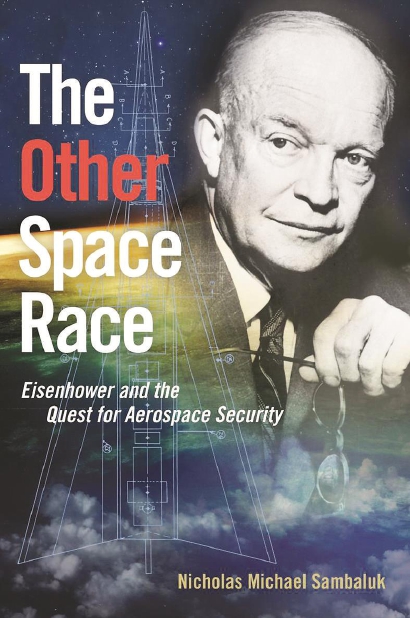
新军事史把传统军事史与经验、社会文化以及内部互动等相联系
您的博士论文尝试把技术史和军事史结合起来研究冷战。在实践中,您是如何利用技术做研究的?
尼克·萨姆巴拉克:历史研究和教学都是需要激情的。在博士论文完成后,我仍与其他研究冷战政策的人有联系,而我的研究也吸引学生,这实现了我的理想和愿景。我最初从技术史的角度考察美国史和军事史,后来在普渡大学我更深入技术领域,利用数码相机和电子计算机等技术,创造性地研究历史。可以说,技术令过去不可能研究的问题成为可能。对我来说,提出问题和寻找事物如何运作、发生及其产生原因是最激动人心的事情,而技术史揭开了事物工作和起作用的原理的奥秘。
您主修技术史,辅修国际关系史,把这两个领域与军事史结合起来研究冷战时期的美国军事史。您如何看待新军事史呢?
尼克·萨姆巴拉克:长久以来,军事史关注杰出将领,军队则听令攻击和征服,这是标准的军事史写法。大概40年前,新军事史的开拓者之一约翰·基根(John Keegan)不 仅 关 注 传统的军事行动、技术术语和左派言论等内容,还关注国家交战双方的相关内容,无论好坏。隐藏的经验如何影响战争?战争对士兵个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此外,战争中的社会和文化,对不同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对我来说,历史是一种时尚,可以将细节和脉络联系起来。新军事史把传统军事史与经验、社会文化以及内部互动等相联系,以探索军事行动的影响。在研究和教学中我发现,将不同方面融合在一起,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军事史,意义深远。新军事史既关注新概念和新突破,也注重从过去的研究中寻找新故事。新旧结合的研究很有意思。
比如,1941年7—8月,德国纳粹军队在基辅附近俘获了70万苏联士兵,传统军事史叙事关注事件后德国军队的进一步军事行动。新军事史则会关注不同国家面对这一事件后的反应如何,他们的应对政策,集中营中所受虐待和隔离对士兵和军官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新军事史更侧重关注战场的文化视角,认为各个部分和因素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
技术往往伴随着战争而不断升级和发展。19世纪末,武器技术不断升级,在英国与南非之间爆发的祖鲁战争中,人们开始运用枪支;在殖民战争中使用机械枪的同时,殖民者也树立了很多敌人,令许多殖民帝国走向衰落。在全球建立殖民地的帝国,经历战争和技术发展,而他们的对手手中武器从无到有,对帝国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以枪支为例,英国的枪支在两战之间取得了长足进步,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曾支持英帝国参加一战,而在战后印度也逐步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甘地在20世纪20—30年代影响力达到巅峰,而在二战中,他的和平主义思想并不希望印度人对抗希特勒,后来又派出200万士兵对抗日本和德国。从一战支持英国到二战伊始反对印度派兵参战,甘地的出发点始终是自主性。二战后,印度独立。
在二战中,很多国家通过技术、政策或策略来提高本国的地位。当时的政策相当丑陋,如利用武器轰炸敌对国,损毁建筑。但是没有任何国家帮助苏联人民摆脱饥饿。我不会为原子弹轰炸做辩护,但是日本在1945年春将大量兵力投入到本国防御,这是一件非常可怕而矛盾的行动。没有人考虑平民,他们的政策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抵抗美国。从技术层面看,日本已经没有战斗机了,于是他们训练成年男子和女性手执长矛作战。他们在学校中受训,孩子们则在课堂上挨饿,孩子们的父母想借此避免遭受美国人的伤害。二战是一场全面战争,每拖一天就意味着更多人的死亡。美国从道德和情感等多方面考虑后,最终在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加快了战争的结束。
1944年,美国第一次轰炸日本时避开了城市住宅区,主要针对军事目标,肆虐的炸弹并未造成太大人员伤亡。1945年1月,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接任轰炸机部队司令后改变了策略,在夜间使用燃烧弹无区别轰炸,利用轰炸机低空飞行投弹,击中目标,非常有效率。有部电影 《长崎》(Nagasaki)就是讲述这个故事的,有65座城市遭受了轰炸。到1945年3月轰炸结束,东京大约有10万人丧生,比广岛和长崎伤亡人数都要多,非常残酷。木质结构的房屋被焚毁,东京大约有半数房屋在一夜之间化为废墟。街道上遍地都是尸体,一个晚上因轰炸而死的日本人大约相当于美国整个二战死亡人数的23%。美国本想利用大轰炸逼迫日本投降,然而未能得尝所愿。于是在3—7月,美国继续轰炸了日本的67座城市,像东京这样的大城市遭到反复轰炸。日本天皇本可以避免日本人继续受伤害,但是日本军方占据主导,他们始终不肯停下战争的步伐,在中国战场每天屠戮3000人。美国人不知道到底应该如何彻底击败日本,而日本坚持不放弃在太平洋战场所占领的大片领土。纳粹已经被苏联和英美军队打败,苏军和美军将着手对付日本,因而日本全然没有取胜的希望。美国在日本登陆,而坚持不投降的日本人把平民动员起来,让他们加入军队,在九州加强了三倍兵力。理查德·弗兰克(Richard B.Frank)的《衰落:日本帝国的终 结》(Richard B.Frank,Downfall: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Empire,Penguin Books,2001)讲的就是这段历史。今天我们回顾的时候,看到了战争在末期展现出了最丑陋、最残酷的一面,而在战争时期,它却是残忍而真实的。所有在九州武装起来的日本人都同登陆的美国人做殊死搏斗,直至死亡。当时美国国内对是否使用核武器存有分歧。美国科学研究的负责人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是主要反对者,但他的理由并非武器本身是否有效,而是在思考美国作为科技尖端,应该如何使用核武器才能最好地为战争服务。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悲伤的话题,也是历史的表现形式。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了解世界,理解人们如何解释自己所面临的挑战,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通过讲述人类的经历让后人理解前人的过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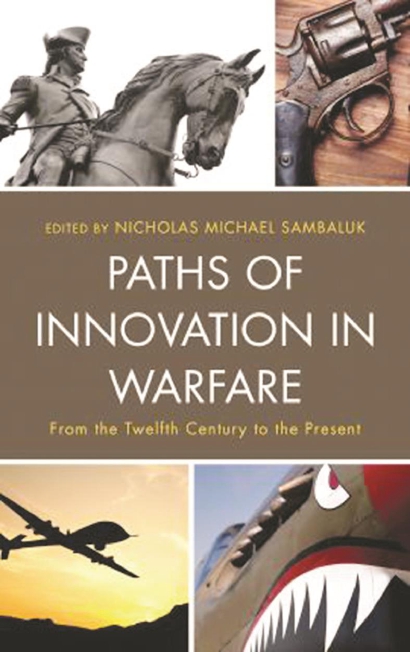
搞明白不同国家寻求救助的过程是很有意义的研究
这些年许多美国史的学者试图突破冷战叙事和意识形态冲突。您如何看待美国历史学界的跨国浪潮?
尼克·萨姆巴拉克:冷战源于美国和苏联在政治体制、经济体系和社会制度等全方位的冲突,从国际主义观点看,这特别复杂。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第三世界加入到冲突之中,有的还通过技术和艺术等形式参与到斗争之中,造成意味深远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相互影响。
从去殖民化的角度来看,战后第三世界国家试图通过技术发展的手段摆脱强国的控制。与之相似的还有法国。法国人不甘心沦为二流国家亦步亦趋于美国身后,他们尝试从原子弹等先进技术等方面入手,以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从而证明法国是独立自主的。
研究跨国史有助于理解复杂的国际关系。国家之间、一国人民与国家交往方式各不相同。二战后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和分歧,例如英国和美国对二战后的世界有着全然不同的观点,在很多方面他们彼此对立;在探讨救助方面,人民又始终是个体,彼此之间的需求不同,因此要建立一个联盟,构建一种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认为搞明白不同国家寻求救助的过程是很有意义的研究。
又比如,在看了1945年之后的手稿我发现,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世界大战的看法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冷战延续自二战,这毫无争议,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我们能看到海量的关于一战的档案,还有一些关于一战的广播节目、舞台剧、电影等文娱图景,如《多么可爱的战争》(Oh,What a Lovely War!是一部史诗音乐剧,由琼·利特尔伍德[Joan Littlewood]创作,1963年在剧院上演;1969年被理查德·阿滕伯勒[R ichard Attenborough]改编为电影)。所有这些都描绘了冲突,在许多战争亲历者讲述中,我们更能了解战争。不同时代的人对战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人和20世纪80年代的人对战争的理解就完全不同。上一辈里的有些人既经历了一战,又从二战中幸存下来。一战给欧洲造成了苦难,很多帝国崩溃了,而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波及范围也越来越广,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历史学家尝试从不同时代的人那里去理解历史,从时代和进步两个维度看待历史是非常有趣的。
作者:文/邢承吉 译/刘雨君
新闻推荐
- 路更顺了家更亲——扩大一次有效台胞证落地办理口岸见闻2026-02-26
- 商务部回应美贸易代表言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2026-02-26
- “马”到成功 澳门新春旅游市场开门红2026-02-26
- 元宵夜×月全食!这场中国境内可见的天象值得期待2026-02-26
- 美贸易代表:美对部分国家加征的“全球进口关税”税率或达15%2026-02-26
- 福马航线迎客流高峰 创历年春节假期新高2026-02-25






